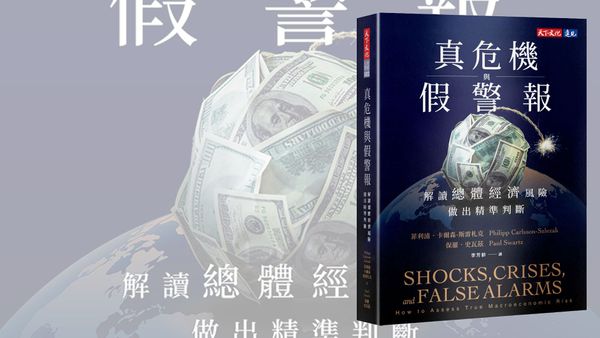2006年,費爾普斯因爲「加深人們對經濟政策長、短期效果之間關係的理解」,而獨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傳統經濟學觀點中,先進國家的蓬勃發展來自探險家、科學家或企業家受新科技刺激所發展的商業應用;但費爾普斯更進一步注意到,一般人為了使工作更有意義、生活更美好,會自動發起基層創新,藉此獲得個人尊嚴和成就感,也使經濟體系茁壯。
費爾普斯構想出一套「大繁榮」理論,試圖超越梭羅的創新構成觀念,強調擁有現代主義價值觀,加上適當的制度,就能產生很多自主創新,經濟更有活力;而且,現代主義價值觀可以讓人民的工作滿意度增加。
他嘗試把總體經濟學建立在個體經濟學之上,將我們所認知的「人類」本質納入理論,讓理論更貼近現實世界。因此,他被譽為「現代總體經濟學的締造者」,也是「影響經濟學進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在這本書中,費爾普斯講述60年來發展這些經濟理論的學思之旅。
二十年來,我苦心鑽研一個可取代約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和羅伯特. 梭羅(Robert Solow)成長理論的新理論,在這套理論中,創新和工作滿意度主要是由經濟中許許多多工作者的「活力」所推動。
這本回憶錄也講述我在經濟理論研究生涯的個人經歷:我曾碰到激進的反對者、與我抱持不同主張的人、低估我的老師,但我也有幸親眼目睹幾位大師的風采。此外,我與創新和經濟成長的主流思想分道揚鑣,用嶄新的角度看待工作和人生,這樣的另闢蹊徑給我很大的成就感。
我的思想發展核心在於發現新想法的興奮,以及創造力的發揮,而非測試或應用別人的模型。我成為理論家,起初是研究過去幾十年備受矚目的理論,但在某個時候,我發覺我過去的理論研究都是建立在其他幾位理論家的突破之上。我一直在構想的新元素,都是用來支持或加強其他人的基本理論,而不是形成自己的基本理論。幸運的是,我能改用新的角度來看現代社會經濟,而且在接下來的十年間建立自己的理論。
我的早期研究是從在耶魯大學的考爾斯經濟研究基金會(Cowles Foundation for Research in Economics)、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與麻省理工學院工作時碰到的一些概念和想法開始,像是儲蓄的黃金法則、公共債務帶來的危害,以及資本投資有「風險」時的影響。我在這些機構工作五年左右。接下來的五年則是在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也在倫敦政經學院和劍橋待了一段時間,並取得一些研究進展,像是在了解凱因斯對薪資行為的觀點上有了突破(亦即「總體的個體基礎」[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還有「均衡失業率」的概念(也就是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所說的「自然失業率」)。這些都在標準經濟學(也就是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和凱因斯主義)的範疇之內。
在接下來的十年,我先在史丹佛大學的行為科學高等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CASBS)做研究,之後去了紐約,不久就來到哥倫比亞大學,也是我最後的歸宿。我的研究焦點也開始從既有的經濟理論偏離。在史丹佛大學,為了回應一九六○年代婦女和黑人的不滿,我在文章中提出「統計歧視」(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的問題。在紐約的時候,我有機會跟史丹佛大學及這個城市裡的哲學家、知識份子就共同關心的議題進行交流。我籌辦一場探討實踐利他主義的跨學科學術研討會,請一群頂尖的學者共襄盛舉,並抵禦芝加哥法學院多位悍將的攻擊。我對社會和道德問題的思考愈來愈深入,我的世界也因此擴展。
我在考爾斯經濟研究基金會做研究時,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的研究室正好在隔壁。他是影響我那幾年的研究最大的人。他的經濟正義(economic justice)概念吸引我撰寫一篇論文,研究實現羅爾斯經濟正義所需的稅收結構。在羅爾斯的著作問世和我的論文發表之後,我一直在想這個社會如何忽視處於劣勢的勞工,這件事教我念念不忘,是我最關注的問題。除了種族與性別平等,經濟正義的概念也是社會思想和政策討論中的新力量。
經濟模型中加點「創造力」
我開始探索一條新的發展方向:重新思考熊彼得在一個世紀前,也就是在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出版的著作提出的創新理論。熊彼得把這一套理論教給他的哈佛學生,例如,梭羅。梭羅在一九五六年把這個創新理論納入他的「成長模型」,這是我和每一個受過訓練的經濟學家都必須研究的模型。
一種新的經濟視角開始在我腦海中成型。這是一種現代經濟,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認為這種經濟一八一五年左右從英國開始,一八五○年代末在美國和歐洲蓬勃發展。我回顧當代標準理論(還有我的理論)時,覺得很奇怪。雖然我和其他經濟理論家一直利用人們普遍具有的創造力和想像力來創造新理論和新事物,但在既有的理論模型中,描述的參與者竟然沒有展現出絲毫的創造力!在這方面,我之前的理論研究和其他人的研究一樣,都遵循既有的經濟學前提,認為經濟參與者不具備任何創造力,也沒有展現出創造力,或者根本沒想過要利用自己可能具備的創造力。這種經濟理論只承認工作的負效用(disutility of work),忽視家庭調查所謂的「工作滿意度」。
同時,我想創建一個完全屬於自己的理論模型,而非延伸或改良其他理論家的基本模型。在我的構想中,我認可一般人的創造力。我開始懷疑熊彼得的創新理論是否能解釋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中葉生產力的爆炸性成長。我覺得我已經準備好建立一套理論,這套理論的基礎是很多人渴望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包括自己的聰明才智和想像力。
這本書不是自傳,雖然我有很多故事可說。相反的,這是一系列的回憶,講述我六十年來的學思之旅,從我早期對既有就業理論的改良,到打造一個全新的創新理論,乃至於理解這個創新過程(在幸運國家當中,約莫一個世紀的蓬勃發展)如何使很多人獲得有意義的工作和美好的生活。
本文節錄自《費爾普斯的經濟探索:實用總體經濟學的開拓者,對失業、通膨與自主創新的思考》,由天下文化授權轉載。